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我与光明日报】
作者:高盈(插画家)
6岁那年,我家搬到虎坊桥老《诗刊》编辑部的顶楼。刚进新家,我踩着小凳子推开窗户,扒着阳台往外看,闯入眼帘的是街对面一栋大大的黄色楼房,在夕阳的辉映下,那一大片深黄,柔柔的、暖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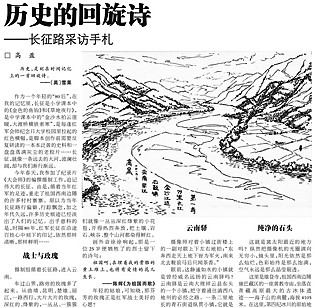
我问:“那是什么地方?”爸爸妈妈说:“是光明日报编辑部。”我说:“这楼真挺光明的耶。”
那以后,跟着爸爸妈妈遛弯,常常经过这栋大楼。大楼院墙外是长长的读报廊,贴满了报纸。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报廊里形形色色的信息吸引我们驻足不前。我总好奇地向报社院子里张望,报纸就是从这里印出来的吗?好神奇呀!
那时我小,不知道姥爷、妈妈和爸爸都在这张报纸上发表诗歌创作或艺术评论,他们写下的文字正是在这里变成铅字。更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也在《光明日报》发表小文。不知不觉间,光明日报留下了我家三代四口人的生命印记。
姥爷是诗人李瑛。1949年,刚刚大学毕业,年仅23岁的姥爷以新华社部队总分社记者身份随军南下,写下《解放一日后的广州》,刊发于1949年10月18日的《光明日报》。从那时起,姥爷开始在《光明日报》发表作品。他写道:“1949年10月1日,我和战友们正在粤北大山冒雨行军,目标是十月中旬解放广州。我们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几千里外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就这样在冥冥之中与共和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多么神奇!那一个个铅字记录下一个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年轻军人身姿,他肩挎枪与相机,怀揣笔和本子,奔走于抗美援朝和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他深入连队,让战士的心声变成报页上灿烂的黄花;他遍访世界各大洲,让友谊的花香飘洒在字里行间……
在周总理去世的日子里,黑云压城,空气异常沉闷。《光明日报》发表了姥爷悼念总理的长诗《一月的哀思》,在全国引发了巨大反响。
姥爷与光明日报有着长达66年的缘分,是同志、老友,更是知音。改革开放以后,姥爷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在《光明日报》刊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春天组诗。每年快到春天时,姥爷都会写一组诗,寄给光明日报。那时,姥爷会颤颤巍巍地递给我一摞草稿纸,随着年纪增大,他手臂震颤越发严重。他用“抖体”写出的诗稿只有我认得,我就把诗稿打印出来。那些诗就像春天的布谷鸟,用最美的词句告诉我们“春天来了”,那是他每年“春天的约定”。姥爷离开后,我在他枕边的草稿纸中发现了一首没写完的诗,歪歪扭扭的文字间,我认出了“春天”“新芽”几个词。这是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送给春天的诗!如果能完成,他一定会把它送到这张传播光明的报纸——《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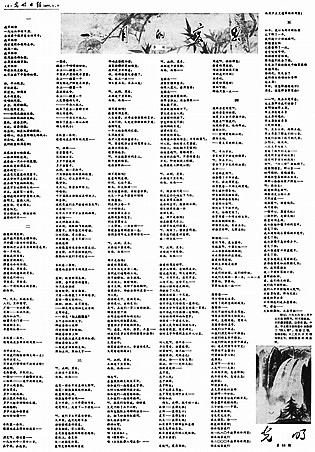
我的妈妈李小雨,也是一位诗人。上初中的一天,妈妈拿着几张稿纸,兴冲冲地跟我说:“你看看,我这首诗写得像不像?”像什么呀?我想。妈妈念道:“我的女儿 总是热情得混乱 总有一个本子或一件衣服 找不着踪影 然后含着泪珠大叫大嚷”“我的女儿 让公主不嫁给王子 让机器猫比水晶鞋好看 让小狼和狐狸都成为她的弟弟。”哈哈哈!原来是写我啊!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暗暗开心。
妈妈离世早,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想找这首诗念给我的孩子听,却怎么都记不起在哪里。没想到,我竟然从妈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作品中找到了这首诗!读着这些句子,好像小时候的我从文字里蹦了出来。
妈妈用文字记录我的童年时光,也记录下她生命中一次次心灵感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她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作品。年轻的妈妈深入胜利油田,用烈火与焊枪为意象描写油建工地的年轻工人,作品见报后,受到石油工人的喜爱。她的反映改革开放时代青年的诗集《红纱巾》在全国范围内有了一定影响,许多年轻人由此爱上诗歌,成了妈妈一辈子的诗友。在《光明日报》上,妈妈的诗行中流露出她多彩的人生和丰富的情感:在抗击病毒的日子里,被白衣战士捂得发烫的听诊器;改革开放后广东小镇里盛开的灿烂小菊花;挂在自行车车把上的方便面、花生米和平凡忙碌的人生……妈妈眼中的世界,感性而富于深意,多彩又充满希望。
我的老爸高鉴,自诩是梨园行中人。从小,他就带我去各种剧场,看了好多舞台表演,戏剧创造的世界对我来说新奇又神秘。
老爸也常和报社文艺部的编辑一起看戏,参加剧目评论会,出席国内外的理论研讨会,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我长大后,看到老爸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很多剧评、综述及杂文。他写东北、内蒙古等地的地方戏蓬勃鲜活的生命力,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他认定戏剧生命力的源头在民间,呼吁让戏剧更广泛地走向民间,去汲取清新的气息和原始的活力……
后来我出差去过很多乡村,看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亭台楼阁上,一台台二人转、梆子、黄梅戏,唱着说着南腔北调,肆意宣泄着情感,热烈或婉转,讲述着从古典到现代的故事。看着这些热气腾腾的景象,我就会想起爸爸在文章里说的“戏剧,要到民间去寻找你的生命之泉”。
我从事纪录片工作后,走过很多地方,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体验了千姿百态的生活。我也想把我的见闻、感受、心情记录下来。想到姥爷、妈妈、爸爸都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作品,我能不能也试试看呢?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参加了纪录片《大会师》的拍摄编辑,循着当年红军的足迹,重走了祖国西南边陲的村村寨寨。一路上,我用文字和镜头记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还画了不少速写。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给光明日报投了稿,报社的编辑非常热情,帮助我修改提高。后来,文章发表了,还配上了我的速写!我高兴得都要跳起来了,能够和姥爷、妈妈、爸爸一起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特别开心、自豪,感叹这神奇的缘分。
20年前,光明日报社迁去了新址。每次路过,远远看见报社大楼,仍会想起我们一家三代与光明日报的故事,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潮涌,眼前又浮现出老报社大楼那一大片深黄的外墙,在霞光的映照下,柔柔的、暖暖的……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4日 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