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察人文以成化,固彝宪而生知”
——冯天瑜的学术人生
作者:周积明(湖北大学教授)
学人小传
冯天瑜(1942—2023),湖北红安人。历史文化学家。1964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1964年至1976年任教于武汉教师进修学院,1976年至1979年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1979年至1994年任教于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1994年之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曾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周制与秦制》等。

冯天瑜
2019年6月16日,“汤用彤学术奖”颁奖仪式在苏州举行,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荣获该奖项。评委会给冯天瑜的颁奖词为:“先生处世,树德立言,以生态、元典之论,独秀前哲。考析华夏文脉,究探先贤骊渊;述上哲之诰,益后辈之思;观澜索源,振叶寻根;钻仰中外交流之脉络,昭晰古今发展之源流;察人文以成化,固彝宪而生知,嘉惠学林,渊哉铄乎!荣膺兹奖,当之无愧!”
这个颁奖词对冯天瑜的学术贡献作了精练概括和高度评价。冯天瑜一生献身于文化思考与文化守望,献身于文化史研究,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有思想的学问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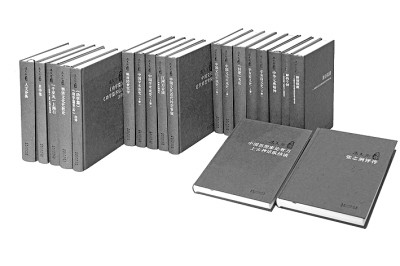
《冯天瑜文存》
浸润书海 尊奉庭训
冯天瑜,1942年出生于湖北罗田三里昄,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父亲冯永轩,1923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师从文字学家黄侃;1925年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其在国学院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即由王国维担任。清华国学院毕业后,冯永轩辗转任教于武汉中学、迪化师范(今新疆师范大学)、安徽学院(安徽大学前身)、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师专(后改为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他一生以治学为业,学术专长包括中国史学史、上古史、西北史地、楚史、古文字及声韵学等。母亲张秀宜曾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还曾到苏联学习俄语,多年任教于小学、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就职于湖北省图书馆。张秀宜是典型的新女性。她效慕秋瑾,曾率百余女子反抗缠足;追求新知,每日手不释卷,于女红、家务则不甚措意。据冯天瑜夫人刘同平回忆,每次去冯家,张秀宜都是在读书看报。武汉大学冯氏捐藏馆中展出的张秀宜书法字迹娟秀,体现出良好的文化素养。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冯天瑜自幼酷爱读书。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冯天瑜一直跟随母亲住在图书馆宿舍。这段时间,他称之为八年“驻馆”时间。八年中,每天放学后,他就在图书馆的书海中尽情徜徉,从小人书一路读到中外名著,从文学、历史一路读到各类游记和地理书。大学期间,他依然如此。他的大学同学几乎回忆不起来他在班上的活动,因为课间时间他多半在读书,上完课,就径直去了图书馆。海量的阅读,使冯天瑜自青少年起就文史知识广博。他对各省、各国的面积、人口、物产、山川了然于心,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与世界各国地图的轮廓。他从屠格涅夫,大、小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等文学巨匠的著作中吸取了思想养料,获得对西方文化的体悟和社会史认知。所有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文化史研究和对历史问题的理解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冯天瑜的人生路途中,家庭氛围的潜移默化以及典藏知识的图书馆都对他有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冯永轩发现幼子冯天瑜对文史有强烈兴趣,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他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以此弥补前面四个儿子从事其他专业带来的遗憾。冯永轩博闻强记,庭训时不持片纸,不仅逐章逐句吟诵经典原文以及程、朱等各类注疏,还联系古今史事,纵横议论。冯天瑜边听边记录,偶尔也插问,父亲就又申述铺陈一番。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冯永轩还常以家中收藏的文物如书画、瓦当、城墙砖以及各朝代的货币作为教具,让冯天瑜和他的哥哥们直接触摸历史。冯天瑜后来回忆说:“这一段庭训的意义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直到后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才深觉它的重要。因为我由泛览进而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入室,学术人生的转折就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这段庭训之间。我时常感叹,自己的‘专业阅读’来得太晚,到青年时代才开始诵读经典,在对古典的熟悉程度上,远不能与有‘童子功’的老一辈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在世界知识和现代理论方面有某些长处超越老辈,但在对本国文化元典的熟悉与体悟方面显然不足,这也是难以出现真正学术大师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父亲的庭训,让我慢慢向后来的文化史研究靠近。”
考析华夏文脉
1979年4月,冯天瑜从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调到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担任历史系副主任。此前几年,他因《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激赏,从武汉教师进修学院调到了武汉市委宣传部。在接受任命时,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不搬家;第二,不坐市委的专车。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冯天瑜还是住在教师进修学院15平方米的房子,每天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武汉牌自行车上下班。他一如既往,沉迷于读书,几乎读完了当时市委图书室收藏的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包括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著作。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是冯永轩老先生任教过的地方,冯天瑜在这里,一方面继承并光大父业,另一方面以此为学术生涯的开端与文化史研究的起飞基地。对于为什么选择文化史作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冯天瑜后来追忆说:“文化史比较集中地体现历史与人民的关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正是立足于这样的人民史观,冯天瑜开始了他的文化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文化史研究热极一时,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于他一直在执着地追问和探寻中华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它的生存机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传递下来?进而去探求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个中心问题,他相继撰写了《上古神话纵横谈》《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国文化生态论纲》《中国文化元典十讲》。《上古神话纵横谈》以文化史视角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上古神话加以诠释,探讨的是“中国神话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中发展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和西方神话、印度神话的区别在哪里?”《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溯源篇》中,冯天瑜对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和文化土壤展开了别开生面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评论说:“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奥秘》在《溯源篇》里论述的几个问题,即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中国文化的‘土壤分析’、农业——宗法社会养育出来的中国文化等,在理论的探索上有格外值得重视的地方。”在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中,冯天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持续深化。1999年,在《中华文化史》中,冯天瑜正式提出了“中华文化生态”的概念,并将这个“文化生态”系统概括为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这三个方面如何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和独立道路。2013年后著成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国文化生态论纲》,提出文化生态四要素说,即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其论不仅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更加缜密,而且把政治制度纳入文化生态,为后来的《周制与秦制》一书的思考与写作埋下伏笔。对“中华文化元典”的解读也是冯氏文化史研究的一大创新。冯天瑜从这些“元典”中掘发出“循天道、尚人文”“通变易、守圜道”“重伦常、崇教化”等“元典精神”,并致力于揭示它们是如何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其蕴藏的基本精神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阐扬,这种元典精神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如何发挥功能。他所关注的还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蕴。
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经《中华文化史》到《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天瑜对中国文化土壤、中国文化特质、中国文化生成机制等问题有了较为完整深入的认识,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界独树一帜。
冯天瑜说,他的文化史研究着重于中国文化史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段,一是先秦——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一是明清——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期。抓住“轴心时代”也就抓住了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抓住了“文化转型期”也就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新变”的关键节点。如果说《中华文化元典》是研究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代表作,那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散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晚清经世实学》《张之洞评传》等则是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的代表作。
《明清文化史散论》汇集了冯天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撰写的若干关于明清文化史的文章。其时,文化史研究热潮尚未兴起,因此,冯天瑜是文化史研究的开风气者。由于冯天瑜关于明清之际思潮的研究承传侯外庐“坚持民主启蒙,批判专制独裁”的学术路线,吴光将其列入广义的侯外庐学派,称《明清文化史散论》颇有外老遗风。然而,冯天瑜虽然服膺侯外庐,但也对侯外庐的论断有修正与新的发挥,如在《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中,冯天瑜就以“新民本思想”修正侯外庐“早期启蒙思潮”概念。名之曰“早期启蒙思潮”是将西方的历史概念嫁接于中国历史文化上;名之曰“新民本”则是真正从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中发掘出明末清初新思潮的生长点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显示了他对明清之际思想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无论是研究明清之际的新民本思潮还是关注晚清经世实学,冯天瑜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发掘走向近代的潜在因子。在他看来,道咸经世实学就是传统儒学面对“过渡时代”作出的积极反应,是近代新学赖以产生的最直接的民族文化土壤,是中国的“古学”通往“新学”的中介与桥梁。他的结论是:中国近代新学的近代性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学赋予的,但它的某些基因深藏在近代民族文化的母胎之中”。也就是说,新学的近代性既来自西学东渐的横向运动,也来自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纵向运动。而明清之际新民本主义与晚清经世实学两大论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虽然尚未正式成为近代新文化,却已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并提供了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融合的结合点”。这个结论是对美国费正清学派“冲击-反应论”的有力回击。
同样,他关于张之洞的研究、辛亥武昌首义的研究,也无不将其放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转型的背景之下加以考量。在张之洞研究中,他试图观察的是,“汹涌奔腾的历史潮流怎样把一个封建士子推上近代舞台,中世纪的固有传统和迎面袭来的‘欧风美雨’怎样促成了他‘新旧杂糅’的思想行径,他的这种充满矛盾的活动又给中国近代历史诸侧面打上了怎样的烙印”。他研究武昌首义,不仅爬梳出大量资料,从总体格局到局部细节对武昌首义进行了更为丰满的展示,纠正了以往研究的种种舛误,更重要的是,“追究这一事件背后的‘中时段’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考察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宏大的眼光、深邃的历史哲学,使得冯天瑜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这是他对文化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历史文化语义学与《“封建”考论》
21世纪以来,在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近代传入与生成的新词汇、术语、概念,对它们进行“知识考古”,“借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对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冯天瑜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中,他就对“文化”一词进行长篇考释,并兼及“文明”;又在该篇第四章第三节《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中指出:“时下通用的‘封建制度’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辨析的概念,因为它的含义既大异于古来惯称的‘封建’,也颇不同于西方史学界常用的‘封建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较早探讨封建概念古今演绎、中外对接间得失的文字。继之,冯天瑜又发表了《厘清概念——以“封建”“形而上学”为例》《“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等探讨术语生成、演化问题的专文,从关键词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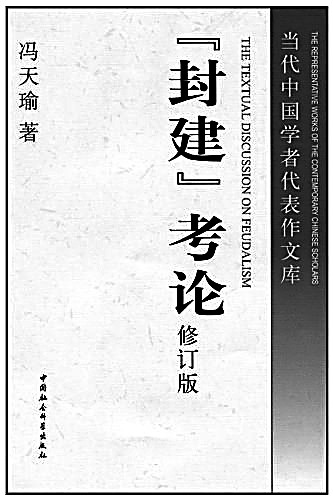
《“封建”考论》
21世纪初,冯天瑜创立了“历史文化语义学”。“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不只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要求论者在对语义进行考察时,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蕴。只有当某一术语或概念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时,它才有可能被纳入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它所关注的是一些关键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术语和概念,通过考察关键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语义变化,探悉由此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涵义。”他欲将“概念史”纳入文化史研究范畴,为“概念”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哲思。
在“历史文化语义学”方向,冯天瑜的代表作是《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封建”考论》。其中,《“封建”考论》是冯天瑜在“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一部堪称经典的著作。
“封建”一词,国人耳熟能详。唯人们习焉未察,“封建”的本来含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因此,“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土经济、贵族政治”。由于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与中国殷周的封建制相近,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武二重制“酷似”,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五四”时期,人们忽略了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受苏俄“泛化封建”观影响,人们把“以农业为基础的”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视为“封建社会”。其后,这一泛化的“封建”概念传播开来,普被九州,在人们的观念中牢不可破。
对于“封建”概念误读的质疑,并非自冯天瑜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谷城、王亚南、瞿同祖、钱穆、张荫麟、雷海宗、李剑农、费孝通等学者都曾对“泛化封建观”提出不同意见。侯外庐甚至称,误读封建,导致“语乱天下”。冯天瑜以恢宏的视野,在中西日互动的架构上旁征博引,纵横古今,厘清“泛化封建”概念的来龙去脉,发掘其语义变迁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内涵,明确指出:“经过多年的考析,我确信,‘泛化封建’观是不能成立的。单从概念演绎史的角度说,它至少有‘三不合’:(一)不合本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二)不合西义(feod意为采邑,又译封地,意谓采取其地赋税);(三)不合马克思的本意。”“‘泛化封建’的确立,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结果。”
《“封建”考论》甫一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维规评论说:“拨乱者,非自冯氏起;而冯氏拨乱,气势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根蟠虽然不同意冯天瑜关于“封建”概念的意见,但也称:“批评秦以后封建社会说的文章多矣,而此书堪称集大成之作。”2007年10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论坛;2008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讨论会;2008年12月,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志琴评论说:“一本著作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进行连续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
压轴之作:《周制与秦制》
2020年秋,冯天瑜开始写作《周制与秦制》。所谓“周制”“秦制”是覆盖中国古代历史的两种政制形态,前者是“帝王赞助儒家阐扬并试图复兴的已然衰微的宗法封建制”,后者是“帝王偕法家构建并厉行的君主集权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周制”与“秦制”既互相博弈又彼此渗透,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形态与转型。

《周制与秦制》
《周制与秦制》的写作虽然始于冯天瑜生命的最后阶段,但此题蕴积于心,约有20年之久。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冯天瑜已经注意到“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政治环境,对文化样态及其走势有甚大影响”。其第九章第一节就是专论“周制与秦制: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由此奠定了《周制与秦制》一书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在《“封建”考论》中,为了辨析“封建”的名与实,冯天瑜对西周“封建”和秦汉以后“皇权时代”的特征有详尽讨论。在《周制与秦制》中,冯天瑜则对中国传统政制形态展开全面的反思和批判。2022年10月26日一早,他在给笔者的微信中阐述他写作《周制与秦制》的宗旨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逐渐成型的想法是,两千余年来帝制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的优长与短板,并非单独由儒或法、周或秦的一个方面铸就,其机制寓于制度层面的实秦虚周、文化层面的儒表法里。故单单‘反秦复周、崇儒批法’,或‘反周复秦、反儒扬法’都无济于事。这一综会再创过程,又有西制、西文可供参酌(不是如法炮制)。拙著《周制与秦制》还在修订中(商务比较宽大,容许我一再改、补),争取把这一旨趣讲清楚。”不久后,他又来微信阐述说:“在下其实极重视周秦之变,以为是中国史上最重要变革,全书展开于此,但又不能简单称秦汉以下全行秦制,遂对中古、近古、现代诸先哲‘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惯说有所补述:周秦变后,又有汉代的复古更化,部分复周变秦,形成‘霸王道杂之’‘儒皮法骨’的汉制,正是这种秦制改良版——汉制沿袭百代,而不单是秦制纵横天下,这大大增强了传统制度及文化的延续力,时至近代,也就成为制度及文化转型的强韧阻力……百余年来讨论同期发生的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何以成败大异,其要因应在此寻找。”他的这些论述,充满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复杂性的洞察力。他讨论的是历史,内心的关怀则在中华民族的未来。
冯天瑜自述,《周制与秦制》是他“这一辈子最在意的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据其弟子姚彬彬说,《周制与秦制》全文初稿约四五十万字,先生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大约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书稿。其后不断加以修订,直到2022年12月26日进入重症监护室前。值得欣慰的是,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周制与秦制》终得顺利出版,上市不久就加印,这是对冯天瑜最好的告慰。
1988年,冯天瑜在《中国文化史断想》的序言中曾自述:“笔者自七十年代末便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40多年的时间,冯天瑜实现了他的初衷。侯外庐曾寄望冯天瑜“成就一个真正学者的事业,为这个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冯天瑜不负侯老所望,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创造了显赫的业绩,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他无比热爱的中国文化。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9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