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苏培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人小传
王锳(1933—2015),四川成都人。语言学家。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遵义师范专科学校、遵义教育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曾兼任贵州省语言学会会长。著有《诗词曲语辞例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宋元明市语汇释》《〈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等。

王锳
学界新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8年时间,我和王锳的人生轨迹基本重合,我们也因此成为挚友。
王锳193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参军,参加过川藏公路雀儿山段的建设。1957年,王锳和我都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同学,1959年又一起被分入语言专门化。1962年本科毕业,我们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由教育局再分配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古代汉语课。我和他同住一间寝室,朝夕相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要讲授古代汉语这样重要的基础课,谈何容易。我们认真备课,争取老教师的指导。那时王锳已经结婚,爱人在贵阳工作。1965年,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停办,王锳去贵州与妻子团聚,我被分到北京女八中做语文教师。
“文革”结束后,《中国语文》杂志复刊,王锳向该刊投稿。京黔两地相距遥远,当时通信不便,他委托我为代理人,稿件如有问题,我可以代他与编辑部商讨处理。这篇文章就是1978年第3期《中国语文》刊发的《诗词曲语辞举例》,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其中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吕叔湘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朱德熙先生这两位著名语言学家。
1983年春,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克服种种困难,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到北大中文系开设语法史专题课,目的是要推动国内的近代汉语研究。在讲座开始前,吕先生和朱先生想到了王锳。王锳虽然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是吕、朱对他并不熟悉,给他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王锳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那篇论文。他们认为王锳是可以造就的人才,愿意尽可能为他提供深造的机会。王锳当时在贵州的一所师范学院任教,要他自己申请离开工作岗位半年到北大进修,还要自己承担费用,是很大的难题。吕、朱二位没有放弃努力,经过协调,北大中文系发函聘请王锳到北大讲学,由北大承担食宿等费用。接到聘书后,王锳整装进京,重返燕园。不过他不是来讲学,而是来听梅祖麟的课程。在那段时间,王锳还跟随吕、朱两位先生去太原参加全国语言学学科工作规划会议,开阔了眼界。

王锳(左)与学生交流。

王锳(左三)与学生在一起。
胜义纷呈的《例释》
王锳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我见到的有十几种,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诗词曲语辞例释》。
在《诗词曲语辞例释》之前,近代学者张相撰写过《诗词曲语辞汇释》。所谓“诗词曲语辞”,按照张相先生的说法,“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诗词曲语辞”实际上就是唐宋以降汉语口语中的新词新义。由于历史原因,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的“雅诂旧义”,对唐宋以下近代汉语阶段口语词汇则很少问津。这不仅造成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大段空白,也影响到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古籍整理,以及对这一漫长历史阶段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突破了传统训诂学取材的狭隘范围,注意到唐以后保存口语资料较多的诗词剧曲,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不过因为这项工作具有开拓性,《汇释》在收词、释义方面,难免有所失漏。王锳的《诗词曲语辞例释》意在补充《汇释》的不足,搜集并诠释其失收的条目,完善或修正其部分条目的释义。在资料来源、取例汇义、编排体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例释》大都能继承《汇释》的优点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进。《例释》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印行,产生广泛影响。吕叔湘在给王锳的信中给予“探微索隐,甚见功力”的评语。北大教授蒋绍愚在《唐诗语言研究》中对《例释》评价说:“在收罗宏富、释义精确方面,此书继承了《汇释》的长处,但所谓补遗,则不仅是收列了《汇释》中未收的条目,而且对《汇释》已收条目诠释不妥与遗漏之处也做了纠正和补充。更重要的是方法上比《汇释》有所改进,首先是注意了词义之间的联系,其次是有了较明确的语法观念……这是一部关于诗词曲语辞研究的高水平著作。”由于学界的推许,该书于1987年获首届吴玉章奖金的语言文字学优秀奖。下面例举《诗词曲语辞例释》(第二次增订本)对《诗词曲语辞汇释》的两处修正或补充。
如,《汇释》卷五“办”字条云:“有办到义;有准备义;有具备义。”《例释》:“‘办’还经常用于主要动词之前作助动词,表示可能,义与‘能’同。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仍以‘办到’等义为解。唐独孤及《得李滁州书以玉潭庄见托因书春思以诗代答》:‘知同百口累,曷日办抽簪?’意谓何日能退隐也。皮日休《奉和鲁望秋日遣怀次韵》:‘破衲虽云补,闲斋未办苫。’司空图《白菊杂书》四首之三:‘侯印几人封万户,侬家只办买孤峰。’均犹言‘未能’‘只能’……另,‘办’与‘得’均有‘能’义,二者往往连用,犹言‘能够’。黄机《乳燕飞》词:‘绣帽轻裘真男子,政何须、纸上分今古。未办得,赋归去。’程大昌《念奴娇》词:‘纵有知闻,谁办得、驾野凌寒秉烛。’”再如,《汇释》卷五“处分”条:“犹云吩咐或嘱咐也,与本义之作处理解者异。”《例释》:“除此之外,‘处分’在剧曲中还可表示‘责备’的意思,其程度较斥骂为轻。《窦娥冤》剧楔子:‘婆婆,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则骂几句;当骂呵,则处分几句。’《酷寒亭》剧一:‘大姐,孩儿痴顽,待打时你骂几句,待骂时你处分咱!’二例显然既非斥骂,又非一般的嘱咐,而是‘责备几句’‘说(他)几句’的意思。《王西厢》三之三:‘怎想湖山边,不记西厢下,香美娘处分破花木瓜。’也是指莺莺责备张生非礼。‘破’为‘了’‘着’义(见《汇释》卷三该条)。《梧桐叶》剧一:‘(卜儿云)你题甚诗?(正旦唱)这词又不是道春情子曰诗云,暗伤神,雨泪纷纷,低首无言听处分。(卜儿云)虽然如此,你是女子,赓和他人词章,是何体面?’义亦同。”可见,《例释》对《汇释》的修正或补充,是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作为支撑的。
《例释》不仅修正或补充《汇释》已有的条目,而且增补了许多条目,丰富了诗词曲条目。下面例举两条:
“更,与类连词,与通常作副词用者有别。皇甫冉《杂言月洲歌送赵冽还襄阳》诗:‘流聒聒兮湍与濑,草青青兮春更秋。’‘与’‘更’互文。杨万里《春兴》诗:‘着尽工夫是化工,不关春雨更春风。’又《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绝句》:‘阿谁不识珠将玉,若个关渠风更骚。’‘更’‘将’互文,‘将’亦为‘与’字义。姜夔《卜算子》词:‘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作者自注:‘绿萼、横枝,皆梅别种。’辛弃疾《鹧鸪天》词:‘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余桂英《小桃红》词:‘早知人、酒病更诗愁,镇轻随飞絮。’石孝友《谒金门》词:‘洞里小桃音信阻。几番风更雨。’王质《水调歌头》词(京口):‘古战场,尽白草,更荒烟。’其义并同。”
“辍,分给。李白《赠黄山胡公求白鹇》诗:‘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辍赠,分赠或转赠。韩愈《病鸱》诗:‘朝餐辍鱼肉,暝宿防狐狸。’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诗:‘唯君浩叹非庸人,分衣辍饮来相亲。’……义均同。由‘分给’义引申,‘辍’有时可径作‘借’解。《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七《与朱行中舍人书》:‘某再拜,般家人蒙辍借,行计遂办。’‘辍’‘借’连言,均表借义……以上‘辍’用于指称物,如用于指称人,则有‘分派’义。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诗:‘幕府辍谏官,朝廷无此例。至尊方旰食,仗尔布嘉惠。’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于此诗之‘辍’字下注:‘疑作缀。’按,此属错疑,盖因不知‘辍’有分派义而然。首句倒装,犹言‘辍谏官(与)幕府’,即分派谏官至幕府之意……按《说文·车部》:‘辍,车小缺复合者。’与车辆的行止有关,很难引申出分给义。‘辍’表分给义应是‘餟’的假借……《方言》卷十二:‘餟,馈也。’从馈赠义引申为分惠于人之义是顺理成章的。”
蒋绍愚所论“注意了词义之间的联系”“有了较明确的语法观念”从这些例子中可见一斑。
《商补》《续编》的贡献
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座谈会。会上制定了《1975—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准备在十年内出版160部中外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就在其中。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汉语语文词典。罗竹风先生任第一版主编,王力、叶圣陶、朱德熙、张世禄、张政烺等著名学者任顾问,华东地区五省一市(鲁、苏、皖、浙、闽、沪)400多位学者参加编纂。此书于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4年出齐正文十二卷、附录及索引一卷。全书收条目37万,总字数5000余万,插图2253幅。通过长期认真研读,王锳对《汉语大词典》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双璧,反映了我国辞书编纂的最新最高成就。但人无完人,书无完书,由于种种原因,《汉语大词典》也存在诸多不足。”凭借扎实的学术基础,王锳对此书提出了很多增补、修订意见,先后出版了《〈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两部专著。
《〈汉语大词典〉商补》共收入600余条商补意见,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立目商补、释义商榷、义项商补、阙例增补、提前书证、引文斠议。如“臂膀”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胳膊”,仅此一义。《〈汉语大词典〉商补》指出,“臂膀”条当补“比喻助手”的常用义,《说岳全传》第四十七回:“本帅亲自出马去,收降这个英雄做个臂膀。”再如“到了”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到底;毕竟”,首引唐吴融诗《武关》:“贪生莫作千年计,到了都成一梦间。”《〈汉语大词典〉商补》指出,《全唐诗》录此诗“间”作“閒”,为“闲”字别体,修订本《辞源》“到了”目亦引作“间”,均误。
《〈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也把商讨的条目分为六类:辨释义、考语源、补词目、增义项、添例证、校引文。如“颁奖”一词,《汉语大词典》:“对在某项竞赛中的个人或集体颁发奖金、奖品或奖状等,给予鼓励。”例句引自1991年3月27日《文汇报》。《〈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指出,此词并非纯粹的现代语词,至迟宋代已见。《册府元龟》卷一二八:“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敕,征讨徐州将士等委吏部度支颁奖有差。”王锳还对释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另,释文过于现代化,‘对在……或集体’十五字可删。”再如“戴高帽子”一词,《汉语大词典》引《镜花缘》第二七回:“老父闻说此处最喜奉承,北边俗语叫作爱戴高帽子。”《〈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指出:“引文之前原有‘多九公道’四字,‘老父’当为‘老夫’之误,‘老夫’系多九公自称。”
王锳不仅对许多条目的编写提出了具体意见,而且对全书的编纂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有一种意见认为,《汉语大词典》应该容纳古今汉语的一切方面,越大越全越好。王锳认为这样的意见值得商榷,“它违背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和原则,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一样,单就汉语辞书这一块说,实现上述目标应该是汉语辞书系列,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哪一部辞书。《汉语大词典》修订,从纵向看应当同《现代汉语大词典》分工,从横向看则应和修订本《辞源》《辞海》以及不止一种古今方言大词典分工”,“辞书修订通常比较注意的是增补的一面,而应该删减的一面往往被忽略”。王锳强调,《汉语大词典》修订,不必计较册数的多少,而是既要补其所当补,又要注意减肥瘦身。为此,他提出了“动小手术”与“动大手术”两种路径,通过小手术、大手术结合,给《汉语大词典》“瘦身”。
王锳所说的“动小手术”,包括三种办法:1.删除释文中的冗余信息。比如“池盐”条释义:“从咸水湖采取的盐,成分和海盐相同。我国西北各地和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产很多。古时量地为畦,引含盐分的沃之,称作种盐,水耗则盐成,即为池盐。”他认为,《汉语大词典》作为语文词典,只需保留前一句或两句即可,其后均宜删去。2.删除错误义项。比如“肮脏”条的“比喻卑鄙、丑恶”义,《汉语大词典》引明周茂兰《王五痴积制钱为佛像五躯送供虎丘禅院》诗:“岂其肮脏存胸次,恭成法相系所思。”王锳认为,“肮脏”有“比喻卑鄙、丑恶”义,仅据这一孤证得出,而且《王五痴积制钱为佛像五躯送供虎丘禅院》是赠人之作,作者不应在诗中痛斥对方卑鄙、丑恶。单就诗题及所引的这一联的对句“恭成”“系所思”的措辞看,作者是在褒扬对方而非贬斥对方,再通读全诗,更可知编者所概括的义项是有问题的。3.删除某些词目。这些应该删除的词目又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割裂文义的假词,如“须管教”条实际上是把“须管”和“教”两词误合为一;其二是生僻的文坛掌故,这应让位给修订本《辞源》;其三是流行区域小、偶见的方言词,最好不收,可以交给专门的方言词典来收录。
王锳所说的“动大手术”,涉及词典本身的性质。他指出,《汉语大词典》作为大型历时性的汉语辞书,原来的编辑方针“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减肥瘦身,统筹兼顾,这一方针可以改“今”为“近”。他建议,《汉语大词典》收词时限到清代中叶为止,此后的任务一概交给《现代汉语词典》以及《现代汉语大词典》。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使词典本身的性质更明确,定位更恰当。作为汉语历史词典,《汉语大词典》只负责解决清中叶以前汉语词汇查考和研究的需要。第二,可以使参加修订的编纂人员集中精力,抓好中古和近代汉语这一大段汉语词汇短板的补充增订,把近年来中古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真正吸收进来。第三,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现当代。现当代汉语不仅变化速度快,而且问题复杂。只管历史,不管现当代,可以增强词典的相对稳定性。
王锳的这些观点,既为《汉语大词典》修订提供了参考,也值得其他语言工具书的编写者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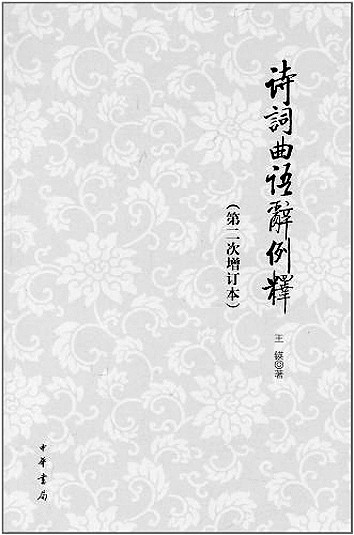

名垂后世
大约是1994年至1995年间,我和老伴王立侠女士去贵阳,参加中国旅游报刊协会评选优秀旅游报刊的活动,几次与王锳相见畅谈。贵阳市区有山,其中一座好像叫黔灵山,在山脚有茶室。我们夫妻和王锳曾在茶室小聚,品茗谈心,十分惬意。
2005年,王锳左肺发现癌细胞,住院做了一次手术。身体康复后,他又在不知疲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一转眼到了2015年,这一年我遇到大不幸,我的老伴患肝癌去世,老伴去世的悲伤一直在折磨着我。这一年的7月8日,我接到王锳从贵阳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右肺,需要住院治疗。我安慰他,要他积极与大夫配合,争取早日康复。过了十天,也就是7月18日,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次很麻烦,癌症在扩散,还要开刀。我除了安慰他,还有别的办法吗?我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出现奇迹。
可是奇迹没有发生,在苦盼了几天后,我收到他不幸去世的信息,许多往事都浮上心头。曾在贵阳山脚茶室小聚的三个人,因癌症走了两人,只剩我一人。王锳调入贵州大学前的职称是讲师,在贵大直接晋升为教授。审阅他的论文并提出直接晋升意见的是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北大中文系1957级语言班有28人,最后成为语言学家的只有四人,就是贵州大学的王锳、复旦大学的孙锡信、北京大学的蒋绍愚和我。时至今日,王锳和孙锡信都去世了,只剩下绍愚和我。
王锳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他热爱语言学事业,几十年埋头苦干,顽强拼搏,为中国语言学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王锳虽然走了快十年,但是他精心撰著的文章仍在社会流传,闪闪发光,造福社会。
本版图片由王锳之女王桢提供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1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