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读书者说】
作者: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出版协会学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最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西北大学出版社奉献给读者的两部考古类的散记和随笔,它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汤惠生教授所著的《观念的叙述:考古学的认知与散记》和《石头的记述:寻访史前岩画随笔》(以下简称《观念的叙述》《石头的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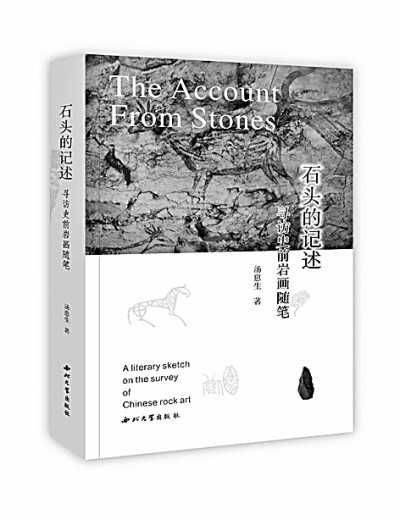
《石头的记述:寻访史前岩画随笔》 汤惠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近十多年来,研究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成果的不断推出,广大读者对我国考古类图书的需求日益高涨。所以,亟待考古学者与优秀出版机构的紧密合作,推出一批内容正确、质量上乘、引人入胜的优秀考古类图书。汤惠生教授的这两部著作内容深刻、思想丰富、文字优美、文图并茂,能给读者提供一种更有见地、更有趣味的阅读感受。在我看来,这两部著作还有以下这些突出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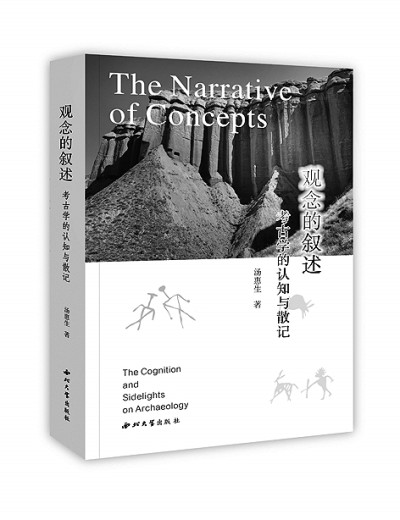
《观念的叙述:考古学的认知与散记》 汤惠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一
该著将早期人类文明放置在人类认识史的视阈之中,把自身长期考古实践中的精细研究转化为文明考古的漫步,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考,既像是体验考古学家场景化的田野调查,又像是聆听哲学家纵横千年的智慧演讲。在《观念的叙述》“孤独考古·寂寞怀旧”一文中,作者把对历史文化遗存的考察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思考结合起来,夹叙夹议,娓娓道来,精彩不断。例如,作者讲述他在青海乐都考察北山石窟时感慨道:“早期佛教石窟并非为人观瞻佛像或接受朝拜的寺宇,而是供僧人修行的禅窟。”“因为心性与佛性无任何差别,清净心即佛性是天赋观念,本无须人为洗涤与布施,所以,只要定心修得了真理,就可以得到真理而成佛。”我经常在想,早期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生活应该都是真诚的和虔诚的,但后来社会中的激励性制度逐渐撼动了人们的精神虔诚。因而早期佛教及其生存状态的宗教性显得十分浓厚,而后期的佛教及其生存状态则越来越倾向于仪式化和观赏性。在这两部著作中,随处可见作者的理论建构和哲学思考,他试图通过系统分析早期人类的思维观念和艺术表达,丰富中国的认知考古学的案例和路径,将早期人类复杂多样的艺术形象纳入一个理论体系和理论阐释之中。
二
该著将早期人类文明放置在具有“一致性”的“原逻辑”世界中观察,告诉我们世界原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我们的思维都是从那个“原逻辑”出发的。在《观念的叙述》“脑洞大开:医术还是巫术”一文中,作者分析了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开颅与碎颅现象,认为都涉及人类灵魂问题并且在各种文化中非常流行,并不认同医术说而主张巫术说,指出这是“要打开通天彻地,知晓过去,洞察未来,通神乞灵的第三只眼或天眼”“人类对命运的追求是无限的,文明的要义就是创造未来。”“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活着是为了享受生活;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活着是为了死去。”作者的这种宗教性和哲理性思考打开了考古思维的天窗。法国著名学者列维-布留尔于20世纪前期撰写的《原始思维》一书中就认为:“原始人的原逻辑不是非逻辑,也不是前逻辑,它是原逻辑。”其实,人类进化的历史并不遥远,原始人的逻辑与现代人的逻辑是相似的,现代人的逻辑是由原始人的逻辑发展而来的。虽然原始人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思维世界中的大量概念性思维,但是在原始人的头脑中却是通过丰富的集体表象来传达他们的思维意境的,尤其是在早期人类留存下来的大量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读者更可以从作者这两部著作中对世界各地早期人类岩画的分析和研究中,深刻体会这种“原逻辑”的相近性和一致性。
三
该著将有关早期人类文明的学术前沿理论知识融汇于丰富多彩的考古叙事之中,并进行了有趣的但不是碎片的介绍,使读者读来津津有味,不觉得枯燥沉闷。在《石头的记忆》“考古·岩画·萨满教”一文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研究与探索的心路历程,尤其值得仔细阅读。作者说:“考古是以物质形式来缀合古代拼图的,也就是说如果涉及古代的精神世界,我们需要看到思想的形状。”“岩画就是萨满教文化的产品,是萨满教观念的图像化表达。”作者认同并发扬了“运用萨满教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考古学。”提出并论述了史前二元对立思维形式正是原始萨满文化的思维方式,从而在中国考古学界发展和深化了结构主义理论。作者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深化诚如作者对结构主义二元论的理论上的逻辑区分,指出对立与统一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分野标志,对立的二元逻辑是结构主义的内核,统一形式下的二元逻辑便不是结构主义。作者认为“只有在区分了二元逻辑的对立和统一形式后,我们才能理解结构主义,才能理解萨满教,才能理解人类文明。”
四
该著将早期人类文明联系的构想以剖析岩画的方式呈现出来,作者讲述了世界各地早期人类留存下来的岩画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思维相似性,也点明了世界各地人类在长期知识积累和接受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人类思维局限性。对象的相似性和认知的局限性形成了人们知识世界的“鸿沟”,而开展“人类认知考古”就有了与历史遗存考古同样的意义。人类认知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走向更加开放还是走向更加局限,文明演进的差异化是否加剧了人们的隔阂?读者从这两部图书中似乎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先人并不是那么狭隘的固守在自己的时空之中,永远不要忘记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可能是人类成长的最大障碍。在《观念的叙述》中有一篇“黄河岸边的考古岁月”,作者讲到1983年湟源大华镇卡约墓地出土的“犬戏牛鸠杖首”以及它所引发的作者的文化思考,那就是原产于印巴次大陆的瘤牛为什么穿越千山万水被铸造成青铜器而出现在青藏高原?或许早期人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封闭和隔绝,他们有着超乎我们认知常识的交往。加拿大学者布鲁斯·G·特里格在《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第一章“研究考古学史”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即“任何东西只有与假设相连才有意义,因为只有理论才能够解释现象。”期待作者在其如此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积累基础上,尽早构建关于早期人类思想以及东亚岩画的中国考古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学者的责任就是在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为我们自己定位,学者的文化职责就是播撒人类文明的种子,减少文明发展的隔阂。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