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光明书话】
作者:陈玲玲(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吴雪莲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屏风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样式,其出现很早。东汉文史学家李尤在《屏风铭》中对屏风的特点进行了描写:“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屏风可以作为摆设,使用时应陈设张立,亦便于收纳。屏风可以阻挡凉风邪气,抵御雾气露水,屏风已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家具,而是承载着儒家道德伦理的具体象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多首诗中写到屏风:“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歌舞屏风花障上,几时曾画白头人。”白居易提示出屏风的另一功能,即将屏视作绘画的载体——画屏。
挂轴于唐末五代被发明之前,中国绘画艺术最重要的两种媒材是手卷和屏风。巫鸿在其主编的《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一书中写到二者之间有两大区别,一是它们不同的“媒介特性”:手卷是时间性的,需要观者以手操纵,逐渐展开;屏风却是空间性的,特别是那些正反两面都绘有图像或题有文字的屏风,更是必须在分隔的建筑空间中观看欣赏。古代画家和工匠利用画屏的这个特点,常在其正反两面描绘和书写彼此呼应的图像和文字,以传达特殊的象征意义或美学趣味。另一区别在于二者不同的使用场合和服务对象。手卷画的创作是为了观者的独自阅览,而画屏则是建筑空间的一部分,既可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又用于陪葬或装饰墓室。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便体现了以上诸多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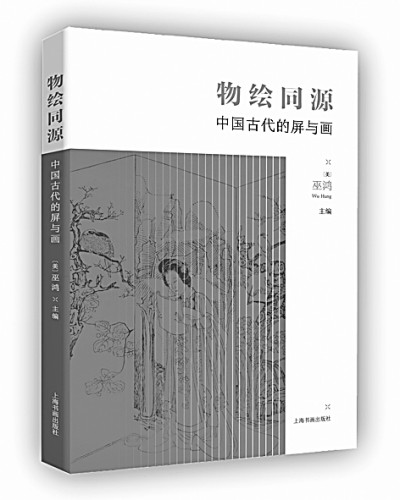
《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
[美] 巫鸿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了建于北魏延兴四年(474)、第二次掩埋于太和八年(484)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司马金龙墓的彩绘漆屏被发现时已严重朽毁,残片散落于各处,较完整的有五块,每块长81.5厘米,宽26厘米。屏风正面的画面题材多为列女,有《有虞二妃》《周室三母》《鲁之母师》《班女婕妤》《启母涂山》《鲁师氏母》《孙叔敖母》等。这些典故大都出自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周室三母》出自《列女母仪传》,画中的三位妇女,容貌矜庄,衣带当风,有着雍容华贵的气度。她们是西周的三位贤后:周太姜(文王之祖母)、周太任(文王之母)和周太姒(文王正妃),她们辅佐周王建立了周王朝。《班女婕妤》出自《续列女传》,画面上有四个人抬着龙辇,上面端坐着一位男子,他向后张望,原来后面跟随着一位美丽的妇人班婕妤,此图讲的是班婕妤辞辇,劝告汉成帝的故事。刘向在《七略别录》中说:“臣与黄门侍郎欲以《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画之于屏风四堵。”从文字中可知,自汉代宫廷起就有了以列女图为装饰的屏风。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上承先秦两汉遗绪,下启隋唐。李清泉在文中将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绘屏风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活中解读。在日常生活中,坐姿的改变导致了屏风尺寸、结构的变化。当时的床、榻家具并不普及,随着人们起居习惯的转变,原本的席地而坐慢慢转向以床榻为坐具的盘腿坐和垂腿坐。进而出现了以屏风和榻结合而成的新型家具——屏坐榻,并在之后广为流传。从目前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屏风实物资料,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赋予这类屏风载体的不同文化趣味。对于画屏中图像的研究,以及画中所绘的屏风物像的研究也为思考艺术史和艺术创作中“物”和“绘”的关系提供了一批重要例证。巫鸿提出,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人已经把屏风作为更大的画面和图像程序中的有机因素,或使用屏风图像分割和规划空间,或用以突出画中的主体人物。唐代开始对屏上画面有了更详细的表现,使之成为整体图像程序中的“画中画”。这意味着屏上的画面和屏外的图像之间发生了种种互动,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绘画的内容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
黄小峰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卷轴绘画时,列举了许多画作,从中皆可看出图像与屏风的密切关联。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为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中,完美地再现了两种形式的屏风:单扇板屏和山字屏风。画中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会棋的情景,四个男性人物在前景中围成一圈或下棋或观弈,童子在旁侍候。全图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戴着黑色高帽的长髯士人,他虽然手里拿着棋盒,但注意力并不在棋局之上,而是神情严肃地观察着弈棋者,心中似有所思。这一中心人物的背后立着一架单扇板屏,屏上图画却展示了内宅生活的场景:一名长髯男子斜倚在床榻上由四个女子在旁边服侍,旁边重屏上所画的山字屏风围绕在床榻边,它作为可移动的家具,与床榻发生关系。画中两个空间之间的平行、对称,突出了府第之中的内、外生活之别。
当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屏风的时候,最大的疑问或许在于“屏风”到底属于哪个艺术门类?林伟正认为:“屏风既是室内陈设组合的成分,也是建筑内部装修的元素,而它所承载的图像又决定了屏风如何完成它被赋予的角色和功能。好像从哪个门类的观点出发,都能够研究屏风,但似乎又没有一个门类能够完全把握屏风的艺术形式和特色。”《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一书的特点恰是将“画屏”这一主题有意识地扩充,其中包括了五位学者撰写的富于专业性而又深入浅出的文章,分别涉及了考古发现的屏风和画屏实物(李清泉撰)、墓葬壁画表现的不同类型屏风和画屏(郑岩撰)、传世绘画中的屏风图像(黄小峰撰)、屏风的类别和历史沿革(张志辉撰),以及屏风在中国建筑中的使用和功能(林伟正撰)。本书在大量考古实物和传统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屏风、画屏和画屏图像的历史证据和发展线索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探讨,在美术史研究中有效运用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使得全书文章有别于把屏风作为一种陈设物件的鉴赏式写作,更突显出此书乃至整个研究项目的跨领域和跨学科的特点。总之,《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一书聚焦于“屏”与“画”的共生,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观照“物”与“绘”在漫长中国美术史中的关联。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