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航满,系散文家、书评人
他们因书与张中行先生相遇,成为行公最忠实的读者,因缘际会,继而成为其挚友、弟子、编辑甚至热心的“鼓吹者”——在张中行与其读者之间,有令后人津津乐道的逸闻趣事,更有令读书人心领神会的那一份投缘与默契。


张中行与范锦荣(右)于北大红楼旧址前合影。范锦荣曾协助选编《张中行选集》。资料图片

1994年8月,张中行与徐秀珊(左)共编《留梦集》目录。 陆昕摄
最早的读者
近期重读张中行先生回忆录《流年碎影》,有一篇《予岂好辩哉》,其中有这么一句:“是1986年晚期我的拙作《负暄琐话》出版之后,谷林先生在《读书》(1987年6月号)发表一篇评介文章,因为我在小引中说到‘逝者如斯’,他就根据《赤壁赋》顺流而下,标题为《而未尝往也》,说了些奖掖的话。好话多说惊动了特级书迷赵丽雅(其时任《读书》编辑),到书店书摊去求,不得,为得虎子,急着入虎穴,写信给负责出版此书的孙秉德,居然讨来一本,还想臭豆腐浮面加一两滴麻油,写信问我,能不能给签个名。字恭整清秀,有筋骨,署名‘赵永晖’。我受宠若惊,立即复信,表示理当遵命。”由此可见,谷林和赵丽雅两人应该算是张中行先生最早的两位读者了吧。如今,谷林和赵丽雅这两位的声名,在不少爱书人的心中也已经是颇有地位,无须我来多作介绍的,后来谷林先生还应邀为张中行先生的《负暄三话》写过一篇序言,而此书中又专门收录了行公所写的一篇长文《赵丽雅》,可算是一段特别的佳话了。
赵丽雅后来以笔名“扬之水”行世,离开《读书》杂志之后,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恰好手边有一套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乃是由其在《读书》杂志工作期间的日记编撰而成,记录了她在那个时期的读书、编辑、交际等事务,尤以与一些为《读书》供稿的老先生的交往最有价值,这其中就包括张中行先生。《〈读书〉十年》后面附录有一个人名索引,其中张中行这个条目就有127个之多,属于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位人物之一。而翻读这些与之相关的日记内容,大多都是取稿之类,但也有些可与行公的记忆相补充,读来就颇有趣味了。诸如第一次拜访张中行,乃是1986年10月19日,日记记录如下:“八点半赶到北大门口,侯李庆西至,一起往金寓(“金”指金克木——引者注)。李与金谈稿,我便去访张中行先生。老两口刚刚摆下早饭,两杯牛奶,小碟上数枚点心:广东枣泥,自来红和大顺斋糖火烧。张先生从相貌到谈吐,令人一看就是典型的老北京,当然居室的气氛也是北京味的。《负暄琐话》书出,在老一辈学者中反响不小,先生给我看了启功先生的书札两通,是两天之内相继付邮的。第一通乃书于荣宝斋水印信笺上,字极清峻,言辞诙谐,备极夜读此书之慨。其后一封言第二夜复又重读一过,心更难平。请先生在我辗转购得的《负暄琐话》上留墨,乃命笔而题曰:赵永晖女士枉驾寒斋持此书嘱题字随手涂抹愧对相知之雅不敢方命谨书数字乞指正。又钤一方‘痴人说梦’印(此印专为此书而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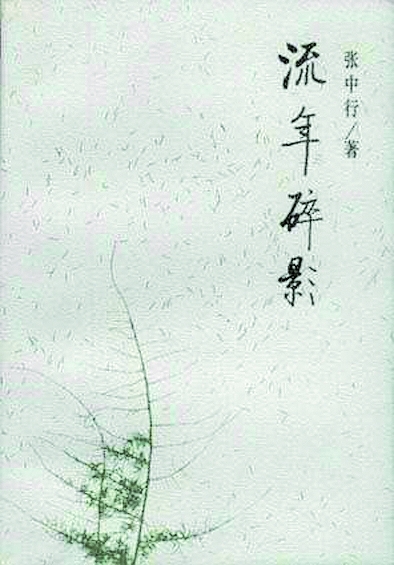
从《〈读书〉十年》来看,扬之水与张中行的交往,除了为《读书》杂志约稿之外,还有两件事情:一是经张中行介绍认识作家南星,这是扬之水颇为感兴趣的文学人物;二是请张中行为其第一本著作《棔柿楼读书记》作序。这两件事情张中行都愉快地予以满足。另外,张中行每有新书出版,都赠书给扬之水,并且还曾为扬之水专门刻过一枚印章,印文为“莲船如是”。由此可见,张中行对于扬之水是颇为欣赏甚至是喜爱的。而张中行笔下的扬之水,简直就是一位当代奇女子,那篇《赵丽雅》就写得颇为夸张。其时,扬之水尚未成名,故而在《负暄三话》中收录这样一篇文章,本来还是有些犹豫的,正如在这篇文章的开篇便写道他选择人物时,常有“犹疑不定的情况”,而“赵丽雅女士就是这样一个,想收,又怕分量不够重,以致说者话不多,听者不过瘾”。但最终张先生不但写了,也收了,而且还特别用力,显示出他的眼光。这篇文章谈扬之水聚书之热、读书之勤和写作之快,乃是连连自叹不如。特别是介绍扬之水的经历,乃是“除了嫁个规规矩矩的高干子弟,生个孩子之外,任《读书》编辑之前,我最清楚的是,大革命时期,也是她的少年时期,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食品店操刀卖西瓜”。
张中行笔下的扬之水的这一行状,如果要列入当代《世说新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最令张中行钦佩的,还有扬之水能够写一手“马湘兰风格的闺秀小楷”,于是便在文章中大大地赞叹了一回:“一个操西瓜刀的能写闺秀小楷,再加上读得多,写得快而好,就使我不能不联想到昔日的才女……”
其实,这其中还有张中行的一个特点,他比较喜欢和有才气的女性交往,这或许与女性多温柔、不具有攻击性有关吧。在《流年碎影》中,还提到两位女性读者,一位名为范锦荣,另一位名为徐秀珊。在《自知乎?自信乎?》这篇文章中,张中行提到除了《流年碎影》之外,还有一套《张中行自述文录》,包括上卷《写真集》,下卷《留梦集》。关于这后者的成书过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是1993年或1994年吧,有一次同范锦荣女士闲谈,曾说到这个设想,只是一本,收写心的,或交处于娘家地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由她编选。她同意,可是我们都忙,说过就置之脑后了。这回记得清,是1994年中期,一阵深情动于中,就由徐秀珊女士协助,把言情的一些篇集到一起,标明《留梦集》,送给一个熟人出版。”
编读之间
张中行先生提及的这位范锦荣女士,任教于北京二中,后来还为张先生编选过《张中行选集》,但未见其有个人著述问世。在网上查阅,范女士系北京二中语文组组长,后来还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的荣誉。在《张中行选集》的《编后小语》中,编者范锦荣写道:“知道张中行先生的名字,约在十多年以前。那时候,我在大学读书,系里一位教授,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张铁铮先生常常谈起他,每次说完,都带上一句特别的评语:‘那老先生没人能比。’我听后,很是惊讶,常想,究竟是怎样一位先生,竟使得我的老师这样敬佩呢?”由此可知,范锦荣女士乃是通过他的大学老师结识张中行先生的。查《流年碎影》中的《汉语课本》一文,有这样一段关于师友的回忆,其中写到从黑龙江大学调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的吕冀平,因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又能谈得来,很快成了张中行忘年的莫逆之交。这位吕先生,后来又回到了黑龙江大学,却让张中行颇感其人“爱人以德”。其中一件就是吕冀平促成了未成名时的张中行著作《负暄琐话》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件则是他对社会上有关张中行早年往事非议的宽慰,乃是劝其“要沉默,而且到底”;还有一件,则是他介绍张中行认识了他的好友张铁铮,很快张中行也与这位张先生成了“莫逆之交”,并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完成了3本《文言文选读》的编选工作。
关于吕冀平和张铁铮的关系,《汉语课本》一文中也有具体谈论,他们曾是“同住哈尔滨的多年好友,好到一生结交许多人,排队,最近的一名,吕的一方必是张铁铮,张的一方必是吕冀平”。由此再联系范锦荣写的那句“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张铁铮”可知,范的老师应就是吕冀平,其人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汉语语言研究上有一定建树,20世纪50年代曾受吕叔湘先生的青睐而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由此似也可知,范锦荣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系张中行好友的弟子之一。这也便可以理解范锦荣与张中行的关系了。1995年4月范锦荣协助张中行编选的《张中行选集》,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制作得甚为精美,精装,竖排,封面书名由启功先生题字,并用张中行先生的手稿作为底图,显得颇为清雅。张中行在此书的《自序》中写道:“我的一位相知许学文先生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工作,有一次同我说,近年以来,我写了内容涉及不同方面的文章出版,他想由他们印一本包括这诸多方面的选集,以飨读者;并抽印二三百本,求纸墨精良,装帧华丽,供我赠友好,不卖,以作为我多年笔耕的纪念。”这本《张中行选集》基本实现了最初的设想,但看版权页,不是二三百本,而是印刷了101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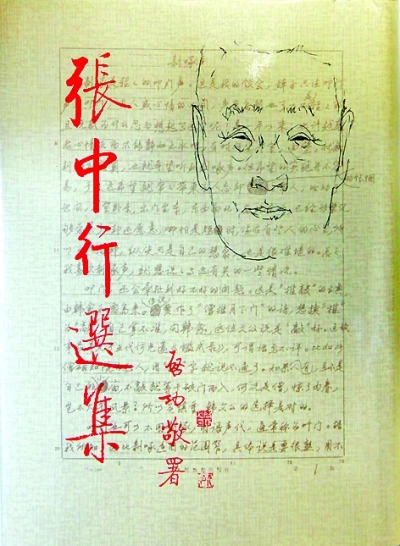
对于这位范女士,张中行先生言语之间,乃是颇为欣赏的。在《张中行选集》的序言中,写到了范锦荣协助他编选的过程,乃是“我选,她补正,她编,我补正,不久就确定了目录”。可见此书其实是二人合作,更深一步来看,乃是张中行对于范锦荣的鼓励。再如回忆录中有《写作点滴》一文,其中这样写范女士编选他的著作《谈文论语集》:“书稿是一九九二年暑假期间,弟子范锦荣(她教中学,只能利用假期)帮助编的,由内蒙古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在张中行的书中,称为“弟子”的,以我目力所见,似乎只有这位范女士。此文还专门写了范女士如何编选此书,用了一段特写,也算是一片情深了:“以后是拖到暑假,约范女士来,商量如何编。由我提出要求,是对一般也读也写的人‘比较有用’,由范锦荣提出取舍的原则,是与‘作意、作法’有关的收,反之不收。原则定,有关语文的文章搜罗来,其余去取、排次序等事不难做。总之,不很久,书稿就完成了,还了愿。”有趣的是,我查扬之水的《〈读书〉十年》,其中附录的《索引》也有“范锦荣”条目,内容系记张中行设宴请上海的郑逸文和陆灏,邀请在座的就有范锦荣。扬之水还特别写了一句范锦荣,如下:“范锦荣一声不吭,任务只是为负翁布菜。”由此可见,范与张中行关系之密切,而这独特的一笔,也能看出张中行对于这位中学语文教师的欣赏。
再来说说张中行笔下的徐秀珊。其实在重读《流年碎影》之前,我就结识了徐女士,并得知她曾与张先生多有交往。这说来还有些意思,大约在两年前,我的老师王彬先生携其夫人过访,其间谈论当下文坛的写作,他得知我爱读张先生的文章,便介绍其夫人徐秀珊曾与张先生颇多交往,还为张先生编选过好几册书。其实我2008年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便结识了王彬先生,可惜不知道他们夫妇与张先生颇有来往。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心向往之的,但待到想结识之时,却为时已晚。张中行先生对于我来说,便是这样的一位。那日说到此处,徐秀珊女士说若张先生还在世,由她引荐结识张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她还答应送我一册自己编选的张中行先生著作留念。第二次我们见面,徐女士果然为我带来了一册由她编选的著作,正是张先生在《流年碎影》中提及的那本《留梦集》,并在扉页上为我签了名。此书后面的折页上有一段编选者的小传,我读后颇为惊讶,摘录其中一段如下:“一九七○年初中毕业。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后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于一九八八年毕业。主要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兼写散文。现在北京什刹海研究会任职,做编书工作。”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发现为张老编书的这位徐秀珊,也是一位与扬之水一样传奇的女性。
收到徐秀珊的这册赠书,我非常高兴,时常拿出来翻读,后来在微信朋友圈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予以介绍:“近来家中装修,翻出一册张中行先生的《留梦集》。张先生的文章或适宜冬日无事,晴窗之下,偶展一卷,可消半日光阴。先生有‘负暄三话’,乃正是冬日闲谈的意味吧。《留梦集》系编者徐秀珊与王彬二位老师过访,知余喜读张先生文章,特意赠予。此册文集朴素雅致,张先生亲自题签,范用设计版式,张守义装帧设计,书前有照片两张,其中一张为张老与编者徐秀珊的合影,由学者陆昕所摄。张老对此书显然重视,特意撰写了序言,范用设计的版式也是别致,每篇文章篇目均为小楷书法题写,甚为清雅,不知何人笔墨,但余疑为扬之水。此册一九九四年秋编成,九五年一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距今已整二十年矣。余生也晚,未曾得识张中行老,得此旧作,也堪为一缘。”其实徐秀珊还为张先生编选过多本著作,恰好我近期得知她出版了一册关于北京什刹海的《春明的眼波》,乘兴也买了一册来读,其中的衬页上便有这样一段简介:“北京城市地理与文化学者。曾任什刹海研究会副秘书长,参与撰写多部志书,并撰写有关研究文章数十篇。主要著作有:《北京街巷图志》《北京老宅门》《胡同与门楼》。主编有《北京地名典》。选编有《留梦集》《月旦集》《说梦楼谈屑》以及《流年碎影》等。”
自知乎?自信乎?
《流年碎影》中还提到多位行公的读者,有一位也是颇值得一说的。在《自知乎?自信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是90年代初期,先来信,接着来人,我交了个很年轻的朋友靳飞,此人的活动能力与年龄成反比,而且惯于起哄,特别喜爱为他赏识的人吹牛。如王宝钏之掷彩球,砸在我头上,之后它见熟人,吹,熟人有不少是编报刊的,于是场地扩大到版面,仍是吹,熟人还有些是在电台或电视台上班的,于是场地更扩大,到电的什么,仍是吹。夫吹,亦如流行歌曲,有传染力,于是有些不姓靳的,也就随着飞,耍笔杆的,写印象记,拿剪刀糨糊的,登印象记,真是热闹得不亦乐乎。我是当事者,常常见到这类吹文,有什么感想呢?”这段话乃是写他对于一些不实之词的反感,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位热诚的读者靳飞,虽然语多调侃,但也显示出一份老实与可爱来。说来也巧,就在我要写这篇文章之时,南京《开卷》杂志的主编董宁文赠送了一套由他策划主编的《开卷随笔文丛》,其中便收录有一册靳飞的随笔集《旧风旧雨》,于是立即翻读了一遍。由此才知道,这位靳飞先生也是很喜欢与老作家们交往,其中与他成为忘年交的,就有严文井、刘绍棠、新凤霞、叶盛长、启功、梅绍武、许觉民、绿原、舒芜、季羡林、刘曾复以及日本的坂东玉三郎等,而张中行先生可以说是交往最深的一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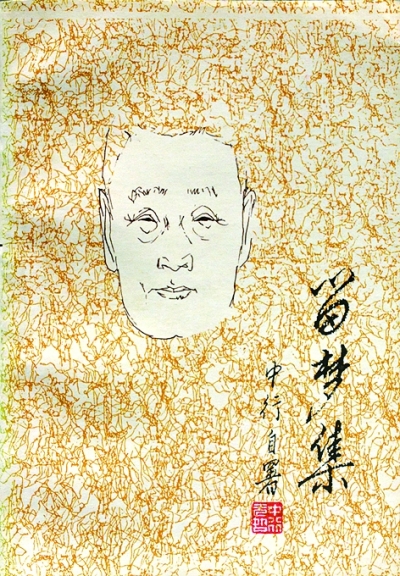
靳飞的《旧风旧雨》中收录有一篇关于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寂寞书斋笔底波澜》,副题为“贺张中行翁回想录完成”,所谈也是与这册《流年碎影》有关。其中写到张中行最看重的几册著作,“曾给他赢得盛誉的‘负暄’系列说,‘就是些闲话儿’”,“为正宗和尚所钦服的《禅外说禅》,是‘佛教基本常识的普及读物’”,而《留梦集》,则是“最为偏疼的孩子”。对于回想录,张先生没有褒贬,靳飞自己评价说:“有如老子一气化三清,那回想录就是他的一个化身。”靳飞的这篇文章还提及他结识张中行先生的缘起,也是颇为传奇:“以时间为序,约在七年前,经常在一起谈文论书的朋友,藏书家谭宗远先生,最早开始在我们的小圈圈里大捧张中行。宗远外刚内柔,见生人专会腼腆,对熟人则又最能不拘礼。他给我这好事的提要求:‘想法联系联系!’”而在结识张中行先生的过程中,靳飞说他先是认识了北京唯一售卖张中行著作的书店老板,并在文章中尊称其为“文雅俊美的摊主李三爷”,并由此在这位书摊主处买了近百本之多,“一来是我有赠书之癖,二来是送书给甲,乙硬索去,甲随即再找我要。有时甚至扯进丙,扯进丁”。这位书摊主也是张中行的读者,在其店中就发生过这样一段佳话,乃是“一位寒素狷介的老妇人用成语词典换走了张书”。此事后来被张中行写成了文章《欲赠书不得》,并收录在《负暄三话》之中。
靳飞在谈张中行的文章中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说,张中行“不拉帮结党互吹互捧,也不故作出或雅或俗的姿态来取悦所谓雅人和俗夫。他的书,就是由读书人及热心文化人,互相传说,辗转购借,情不自已地奔走相告,评价议论,因而成为流行。我是一例,类似我的,至少我知道在深圳有姜威,在广州有许石林,在武汉有徐鲁,在北京有谭宗远、赵丽雅、姚苏敏……举不胜举”。随后他又写了一个自己推举张老文章的故事,而恰恰是这件旧事,令我对于这位靳飞先生更是刮目相看。此事起因乃是靳飞从一所中学调到一家报纸编辑副刊,本是一件颇为高兴的事情,然而此时“行翁不待我约稿就写稿来,而且显见是针对我所在的报纸,不是随意拣出一篇来应付”。从此可见靳飞对于行公发自内心的尊重。由于当时张中行先生还不是太出名,故而靳飞专门为报社写了一个长篇的编辑意见才送审。总编辑看出靳飞的“过于热心”,教育其“做编辑不要总发熟人的稿,这也是必要的职业道德”,后来清样排出,张中行1500字的文章被删成了800字。他问总编辑何故如此,答曰:“给你们发了就不错。”靳飞由此终于是“按捺不住,立即摔了铁饭碗,揣着稿子便离开了那家报社”。
由此可见,靳飞确实是一位真正热爱张中行先生的读者,真可谓是不遗余力地为张先生鼓吹。而用靳飞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认为张先生的文章,乃是“以平生枯寂所积蓄的生命与智慧的光芒,冲破属于时代的苦痛与现实的纠缠,挺身于世纪之交,引导后者复归平静,倡导社会的文明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