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鲁迅借《狂人日记》所发出的“呐喊”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温这部文学经典,回溯这位“狂人”所走过的漫长曲折但堪称伟大的道路——
月光穿过一百年
——纪念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
作者: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周树人到鲁迅
1918年4月的一天,周树人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题目定为《狂人日记》。手稿交给《新青年》杂志发表之前,他第一次署上了“鲁迅”这个笔名。
写这篇小说那年,鲁迅37岁,已经走到人生的中途,无论经历还是心态,他都不是单纯的毛头小伙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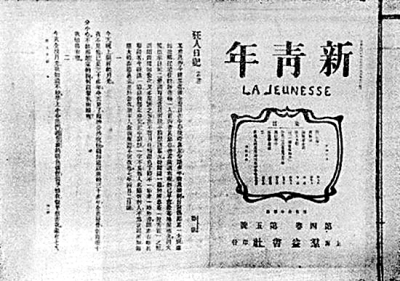
《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
事实上,因为家道中落和父亲早亡,鲁迅的童年结束得远比同龄人早得多。他“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他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和他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上去买药……就这样在无望的努力中,最终无奈地送走了病床上的父亲。穷与病,固然是生活给予少年周树人的最初打击,但更深入灵魂并伴其一生的,是这段经历所带来的精神上的黑影,这黑影,终生啃啮着他的内心,却也催迫他脚不停步,一直找寻着走出这片阴翳的道路。
这黑影,来自“世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是“这途中”所见的“世人的真面目”,造成了少年周树人敏感、倔强、自尊、多疑的性格,也造成了他善良、同情、推己及人、反躬内省的处世思维。他一生心地温软又嫉恶如仇,他一面洞悉“世人的真面目”,看透各种伪善嘴脸下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也一直深切关爱着那些与他同样受过侮蔑的弱小者,直到晚年,他仍在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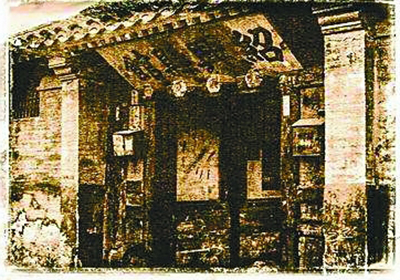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期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
也正因为“这途中”的遭遇,让鲁迅看到了比穷与病更糟也更难战胜的,是心理上的疾患和精神上的顽症。后来作为文学家的他,固然也在笔下叙写贫病交加的底层人民的惨状,但更让他愿意花费笔墨和心血的,一直都是透视他们的灵魂,剖析他们的精神。
37岁之前的周树人,“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绍兴到南京,从仙台到东京,学过水师、路矿和西医,“异地”去了多处,“异路”也试着走了多条,最终走到了文学的路上。他自己后来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那个曾经美满的医学梦是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破灭的。因为在那异国的课堂上,他碰巧看到一个有关日俄战争的新闻幻灯片,里面出现了他“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课堂上的周树人深受震动。除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之外,被刺激的应该还有他那份少年时代的特殊记忆,那些“世人的真面目”的暗影此时一定又笼住了他的内心。麻木的神情、冷酷的内心、势利的嘴脸,对弱者的欺凌、对强权的卑怯、对血腥的恶嗜、对暴行的漠然……凡此种种,都从个人的创伤记忆扩大为对更广大的人群和现实的忧患。于是他想通了一件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弃医从文的周树人25岁,那是一段短暂的青春。呼朋唤友提倡文艺的他,有过几天血气方刚、心怀理想的日子,但很快就在现实面前得到了教训。“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寂寞的人做寂寞的事。从1912年起,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就寓居在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里。过早进入中年的他,就在这座古城中的古屋里,抄些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用”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他的生命就这样“暗暗的消去了”。直到1918年。
从1917年9月30日中秋节的这一晚开始,周树人的日记里开始出现“钱玄同来”的记录。到这年年底,有案可查的“钱玄同来”有4次,而12月23日的记录略有特别,专门记为“晚钱玄同来谈”。一字之别,写日记的人在这个“谈”字里应是着意刻下了对某些特殊话题的记忆。
1918年年初开始,“钱玄同来”得更勤了,2月来了4趟,3月来了3趟,且从“晚”来变成了“夜”访,多半都不是顺路坐坐,而应是有话要说、有事要议的。
不知在哪一次“来”或“谈”的时候,钱玄同提议周树人“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后来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已经在寂寞的苦汁中浸泡多年的中年周树人深深懂得“新青年”的寂寞。他对于再次“叫喊于生人中”感到有些犹豫,但对方的乐观和热情又难免会打动他原本“做过许多梦”的内心。他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人:理智上清醒冷静,感情的深处却常有炽烈的燃烧;内心绝望的同时,却也隐隐期待着热力与行动的拯救。他最好的朋友许寿裳就曾用“冷藏情热”四个字来形容和总结他。
总之这个“冷藏情热”的周树人“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外墙浮雕(局部)
《狂人日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37岁的中年鲁迅,提笔写出的第一篇小说,为什么竟是一篇看似没头没脑的“疯话”?以他的性格和才华,特别是以他深刻的思想和各方面的蕴积,这个写作的开端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如何一出手就将多年的蓄力凝聚在一记重拳之中,这是鲁迅必定反复思量过的问题。
《狂人日记》就是这第一记重拳。事实上,它确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发出了现代中国的第一声“呐喊”。一方面,它在思想内容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揭出封建伦理“吃人”的本质,并以“救救孩子”的呼声开启了那一场以“掀翻吃人的筵席”为理想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它又以“新奇可怪”的艺术效果开创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审美方式,在它“异样的风格”中,给人带来“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沈雁冰《读〈呐喊〉》)。
说它“新奇可怪”,是因为它第一次用口语式的白话直接发出了一个“活人”的声音。那个时候,钱玄同他们那帮“新青年”朋友中,已有陈独秀、胡适举起了“白话文学”的旗帜,提出用“活的文字”写“人的文学”,不再摹仿古人的言语和腔调。但旗帜归旗帜,用白话写成的文学还只是理想。鲁迅并没有写过倡导“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论文,但他实打实地写出了第一篇白话体的短篇小说。
而且,在这篇小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代标点符号。他大量使用问号、叹号、省略号,并真正发挥了这些标点符号的作用,使其参与了文学的表达。正是在这些叹号、问号、省略号里,读者读出了“字缝”里更复杂的意思。比如,为什么“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后面用的是问号,而不是句号或叹号?这里面的意思,有心的读者自然愿意追索,也能够懂得。
当然更重要也更称得上振聋发聩的,还是《狂人日记》的内容与思想。这些乱真的“疯话”中,处处闪耀着双关与象征的光芒,即使再愚钝的读者也能知道,这满纸的疯话其实都是寓言。因而,这些出自狂人之口的语无伦次的“荒唐之言”的一部分,后来都成了箴言警句,透露出深邃睿智的思想。比如,“救救孩子”;再如,“从来如此,便对么”;又如,“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最大的“发现”,就是看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这吃人礼教的虚伪,因为“吃人”是不被直接写进历史的,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在每页“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才看得出来。很难想象,不借助狂人之口,鲁迅怎能以如此当头棒喝的方式,最直接最形象地说出他对中国四千年历史的洞察?又怎能这样正中要害、直击人心,给读者带来那“一种痛快的刺戟”?
此外,鲁迅比别人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他让狂人在吃人的筵席上看到了自己:“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个发现前所未有地清醒和深刻,它提醒每一个人反身拷问自己:虽然“自己被人吃”,但未必没有加入过吃人的筵席。在一场吃人的盛宴上,不掀翻桌椅、不明确拒绝、不主动反抗,都会在事实上变为吃人者的帮凶与同伙,有意或无意地,变成一个同样沾有血迹的“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就这样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第一次照彻狂人的心扉,叫醒了他的灵魂。告别了“以前的三十多年”的“发昏”,觉醒者感到“精神分外爽快”。但与此同时,他直觉地感到了害怕,因为在蒙昧的庸众中醒来,他意识到自己必被视为异类,必将在尚未发生改变的旧秩序中遭到迫害。他“怕得有理”。
这种怕,是每一个“活的人”的本能。怕死才意味着有求生的意愿和自觉,就像临刑前的阿Q,终于在看客们饿狼一样“又凶又怯”的眼光里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一次,“精神胜利法”不奏效了,阿Q想喊“救命”,但话未出口,“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阿Q最后的怕与狂人最初的怕是一样的。与鲁迅笔下其他很多懵懂地生、糊涂地死,从不知道害怕的人物相比,懂得怕死和喊救命的阿Q和狂人,算是接近了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狂人与阿Q还是不一样的,阿Q未及出口的“救命”说明了他也没来得及醒过来,而知道怕的狂人,在月光下,是真的醒了,而且从此“横竖睡不着”,再也不会堕回原来蒙昧的状态中去了。
醒来的狂人意识到危险,却逐渐克服了恐惧。他说:“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越来越“勇气百倍”的他开始不断地向周围人发出他质询、控诉和警劝。没有人听、没有人信,那也不怕的;被人关起来、当疯子看,还是不怕。他“偏要问”“偏要说”,偏要告诉这个自以为正常的世界,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狂人看到并相信,“跨过这一步”,一切便会不同,这一步,就从“说不能”开始。对“从来如此”的那一切,说“不能”;对吃人的筵席,说“不能”。他相信,“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他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狂人日记》不仅是《呐喊》的首篇,更算得上是鲁迅全部作品的总序。它提出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延续在鲁迅及其追随者们后来的作品之中。比如“吃人”的问题、“立人”的问题、“看客”的问题、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被提出、不断被思考,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血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固然是一部经典,但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标本。它是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由这个大门进去,开始了一条漫长曲折但堪称伟大的道路。
茅盾说,读《呐喊》“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这是恳切实在的话,是读者与批评家的实感。但是说到光,我倒觉得将《狂人日记》比作“耀眼的阳光”还是不如鲁迅自己笔下的月光来得更确切。“呐喊”的力量,在那个漫漫长夜之中,划破黑暗,带来苏醒,但它甚至还不能作为黎明时的第一缕晨曦,因为“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知道,那一束叫醒狂人的启蒙之光,或许还是微弱的,但在夜色里,它是“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们的慰藉和方向。
《狂人日记》之后:“坦然地……走,月光底下”
狂人醒过来了,但暗夜仍未过去。月光下的狂人是清醒的,但现实中的他也如年轻时的鲁迅本人一样,会寂寞、会消沉。鲁迅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他转而去思考更重要也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梦醒之后,出路在哪里?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这也是他自己一直在经历着的苦痛,他想要寻求解决的方法。
其实,在《狂人日记》前面的文言小序中是有个交代的:“余”去探望狂人的时候就得知他“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对于这个结果,研究者已经争论了一百年,大家追问的是:这个“赴某地候补”,究竟意味着狂人恢复了常态,还是隐埋了内心?这究竟是他的堕落或投降,还是他的自暴自弃?难道,是他选择潜入暗夜,在隐忍中继续苦闷的摸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鲁迅那里去。
事实上,狂人之后,鲁迅笔下还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的人物。包括夏瑜(《药》)、N先生(《头发的故事》)、吕纬甫(《在酒楼上》)、疯子(《长明灯》)、魏连殳(《孤独者》),以及实有其人的范爱农(《范爱农》)。他们并不都“狂”,但都多少有些迥于常人的行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孤独者”魏连殳。
魏连殳的古怪和另类是闻名乡里的。他样貌奇特、做事不拘常理,言行都是“老例上所没有”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他祖母大殓的仪式上,他不像一般孝子贤孙那样规规矩矩地哀泣,而是突然迸发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魏连殳这一哭,也是哭自己。旷野中的悲哀寂寞和深刻的孤独,是在鲁迅笔下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正是这个孤独的怪人,失业碰壁走投无路了很久,最终突然从政,“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了。在常人眼里,他“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每天“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鲁迅的笔墨却并不重在这些狂怪异举,而是字字血泪地描画他的孤独。在魏连殳写给“我”的绝笔信里,他说: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魏连殳的自暴自弃源于彻底的绝望,他终于在这条自己选定的死路上迅速走完了余生。他并不是自甘堕落,事实上,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成为旧秩序的一分子。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好”了的那个魏连殳,会是那个“赴某地候补”的狂人吗?
《孤独者》当然并非《狂人日记》的续篇,但是,在鲁迅的心里,狂人的去向和魏连殳的出路必定是有关系的。而且,在亲身经历了“五四”落潮和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之后,1925年写作《孤独者》时的鲁迅只会比1918年发出第一声呐喊的时候更增添了悲愤和无奈,对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也必有更多更深的体会。
与魏连殳殊途同归的还有鲁迅的好友范爱农。在现实中,范爱农可能是一个比鲁迅更清醒更深刻的觉醒者,这一点从他们在东京为是否因徐锡麟被杀而给政府发电报的争论当中就可以看出。但就是这个更清醒更深刻的范爱农,同样逃不出走投无路的困境:从学界失业之后“什么事也没得做”,终于也没有人“愿意多听他的牢骚”,只能在孤独绝望中郁郁而终。范爱农的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作为深知他的挚友,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并且相信“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范爱农最终的“直立”姿态让人联想到魏连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样子,前者的宁折不弯和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与精神的最好象征。
这无路可走的真实状态,就是鲁迅在狂人醒来之后提出的比“醒”本身更加沉重的问题。当初,在钱玄同动员鲁迅写作的时候,鲁迅曾以“铁屋子”的寓言征问过他这位激进的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虽然最终,因为“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的希望,鲁迅开始为《新青年》做文章,但事后看来,这个疑问始终没有被他所淡忘。
在鲁迅的笔下,从一开始出现的就是那几个“较为清醒的”“不幸的少数者”,他们在他的笔下,无不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且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入死灭。这并非是鲁迅冷酷无情,而是作为思考和写作者的他其实也并没有寻到出路,他没有办法为他的人物预设一个完满的结局,因此他选择用清醒的笔写出这无路可走的痛苦。
同样处境的鲁迅本人,也正是在这没有选择的境地中做出他的选择的。他常常绝望,但也常常勉力而行,来克服和反抗自己的绝望。就像他在《孤独者》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与自暴自弃或幽愤颓唐相比,鲁迅的选择既简单又倔强。他选择“走”,选择行动。即便仍然走在“月光底下”,走在暗夜中,但只要还能“走”、还在“走”,就仍有希望。就像他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句话,或许正是鲁迅本人对于当年“铁屋子”之问的自我解答,甚至也是他一切写作与思考的基点。《狂人日记》之后的鲁迅,在“月光底下”的道路上,一直孤独顽强地前行。
现在,这月光穿过一百年,照在我们前面的路上。
(作者:张洁宇,著有《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