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画家一直认为,在所有的扶贫项目当中,智力扶贫效果最佳。他下决心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掌握绘画技能。
初到娜姑
云南会泽县的娜姑镇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又是乌蒙山区特殊的贫困乡镇。由于这些原因,娜姑很早就被人们所熟知了。我和娜姑结缘,是在2003年年末。
那一年,我们单位挂钩娜姑扶贫,我刚好被选拔为第一批扶贫队员。出发的那天早上,我正准备乘坐长途汽车到娜姑去,一个圆脸、头发很长的小伙子急匆匆地找到我说:他姓王,是北京来的画家,要跟我同行到娜姑扶贫。北京有位画家要去娜姑扶贫,我早听说过这事,单位领导也曾叮嘱,要我一路上多关照他,毕竟人家是远道而来的画家,不想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娜姑扶贫,我们有计划有目标有任务,要做的事很多。王画家没多少具体任务,整天在镇上“游荡”,我说这样不好,大老远地来扶贫就要做点实事儿。王画家对着我嘿嘿笑了笑,说是让我放心,他正在寻找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扶贫项目。几天下来,王画家神秘地告诉我,说项目已经有些眉目了,要我一起去看看,帮着参谋参谋。经不起他的再三恳求,我只得放下手中的工作,陪同他去看那扶贫项目。
王画家这人很有意思,属于那种“见面熟”的性格。一路上,在他滔滔不绝的自我介绍下,我已经对他的基本情况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某美院油画专业本科毕业,曾参加过两次全国美展,热衷公益的扶贫志愿者。我只管听,不太多说话,年轻人总是充满激情,但谈得再好,关键是要能做,我不知道这位能言善辩的年轻画家,在扶贫上究竟能做出些什么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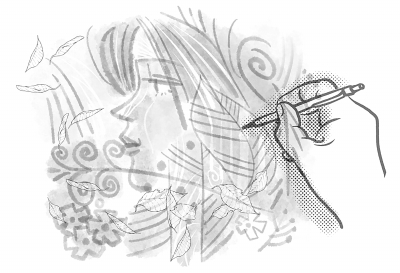
插图:郭红松
王画家带着我来到镇上的江西会馆。江西会馆是镇上保存非常完好的历史文化遗迹。如今会馆正在修缮,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放了,厚实的大门上,一把铜制的将军锁稳稳地钉在上面。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清晨,我们围着会馆转了两圈,也没见到一个人影。我不知道王画家拉着我到这地方是什么意思,他却是一脸的兴奋,说是计划利用会馆里的大殿,搞一些美术方面的活动,把大家的兴趣爱好引导到学科学、学文化上来,搞智力扶贫。在我听来,这计划理想的成分比较多,但我不想扫他的兴,只顾低头走路。我们又转了几圈,王画家突然发现,会馆后院转角处的墙体裂开了一条缝,只要侧转身体,紧贴墙面,人便可以轻松地进去。于是,我们悄悄地进到了院内。
院子里出奇的清静。两棵柏树上停着无数的鸟,发出密而急的悦耳叫声。大量被拆下来的建筑材料——圆的石柱、磨得发亮的青石板、十分精巧的彩绘门窗,整整齐齐堆放在墙角,我们仔细看了看这些建筑材料,上面大多绘有精美图案,造型考究,制作极其精细。我们俩一边观赏一边被古人的工匠精神所折服。
王画家尤其兴奋,索性打开速写本开始写生,我不愿打搅他的工作,便独自围着院子四周散步,刚走到大殿门前,门突然吱啦一声开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站到了我面前,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还没开口,老头已经瞪着眼睛看着我和王画家: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们没料到会遇上这么个人。我指了指转角处的那道裂缝:“从院子侧面的那道裂缝里钻进来的。”我微笑着对他说。
“你们不知道这里正在修缮?你们是哪里来的?”
老头子嘴上说着,眼睛却在盯着王画家手里的一块彩绘板,这是刚刚拆下来的一块破损件,虽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彩绘的颜色已经褪得模糊,但上面的精彩图案仍然十分生动。王画家正画得聚精会神,因彩板上布满了灰尘,实在看不清,他就用指甲在上面刮了刮污渍,不料,这一举动刚好被老头看到了,老头一个箭步奔上去,一把将彩绘板抢到了手里,睁大了眼睛对着王画家吼道:
“彩绘板不能乱擦乱刮,这样要糟蹋了祖上传下来的宝贝的。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我一看老头凶巴巴的样子,知道又遇上了一个不好对付的人物,连忙笑嘻嘻地递上一支烟,小心地说:“我们是来镇上扶贫的。这位画家姓王,是北京来的。”
听了我的介绍,老头愣了一下。他抬头打量了我们一会:“哦,扶贫的,去年前年也来过两个,都走了。”
短暂的交流后,老头的态度明显好了起来。他推开大殿门,让我们进去,说是要给我们介绍这里的情况。我们谢绝了他的盛情。临别时,老头对我们讲,他姓管,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在文化站干了十几年,现在主要负责会馆的修缮和接待来访的客人,介绍镇上各个会馆庙宇古籍的情况,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
我对老头的热情反复表示感谢。王画家却皱着眉头,礼节性地看了老头子一眼,嘴角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我看得出,他对老头子并无好感。
王画家明知自己要搞文化扶贫,肯定得请老管帮忙,可就因为那次不愉快的见面,他有意避开老管,急匆匆找到镇上的领导,把方案一说,大家一讨论,最终镇领导还是让他去找老管,因为这些事老管办起来会更顺手些。王画家也倔得很,面对教室和生源这俩大问题,也不愿意再去找老管。我和他憋了一上午,也没想出办法,最终只能同他一起,挨家挨户去发动,让所有在家的孩子空闲时都跟他去学画画。王画家一直认为,在所有的扶贫项目当中,智力扶贫效果最佳。他下决心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掌握绘画技能。
大约是镇上的领导给老管打了招呼,办班的地点是他帮忙找到的。老管虽然没经常来找我们,但还是默默地帮了很多忙。王画家热情极高,每天起早贪黑,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筹备,美术培训班终于开办起来了。那天,我们俩早早地去了教室,可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好不容易才等来了两个孩子。孩子们进来后,先是深深地给我们鞠了一躬,才怯生生地坐到了角落里。王画家走过去,笑着同他们拉着家常,一边说还一边用手轻轻抚摸了孩子的头,一个孩子竟然吓哭了。王画家不知所措,连忙退到了教室外。原来是两个孩子怕生,见王画家一出教室的门,转身就往教室外面跑去。这下可糟了,我们花了大半个月时间动员来的学生,一晃眼又走了。王画家失望到了极点,呆呆地看着我,泪水在他的眼眶里直打圈。
我见他那委屈难过的样子,连忙跑过去安慰他说,扶贫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还得耐下性子来,慢慢找到好的办法。王画家咬紧下唇,半天没说话,泪水终于流出来了。
那一次展览办出了些影响,镇上几十里地的人都跑来观展,热闹了好一阵子,王画家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得自己干了件大事儿。
山沟沟里办画展
之后的一段日子,王画家整天没精打采,总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担心他憋坏了身体,一直有事无事地找他说话。这天午餐以后,我有意要拉着王画家出去走一走。刚出门,远远地就看到老管朝我们这边走来。王画家心中不舒坦,想避开老管,可老管已经来到面前。老管看到我们,也没什么好脸色,瞪着王画家说:“要办美术培训班,也不先打个招呼,像你们这样办班,能办得起来吗?那天你们开班就来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父母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带着,学校放假了,没人管他,就送来交给你们了。另一个孩子是生病住院刚出来,只当是送到你们这里养病来了。你们不讲清楚上绘画班以后能干什么?能起到个什么作用?对他们以后养家糊口有什么帮助?不把这些讲清楚,还会有人来吗?现在的人都是很讲实惠的。”
王画家一肚子的委屈,但见老管讲得有理,也就压压怨气放下架子,堆下笑脸说:“那你说该怎么办?”老管说:“就下周六吧,你们只管负责教学的事情,发动学生的事就交给我了。”王画家半信半疑,点了点头。我心里也没一点谱。老管说的话,能靠得住吗?
周六很快就到了。天黑以后,我和王画家向教室出发。一到教室,我们就被惊呆了,坐了满满一屋子孩子,不时有几个调皮的孩子跑到门口张望一下,翘首以待他们新来的美术老师。王画家一下子兴奋起来,重重地在我肩膀上捶了几下,一步跨上前去,紧紧地搂住老管,就差在他胡子拉碴的腮上亲上一口了。
开学后的课程安排得很紧凑,王画家首先给他们讲西洋画简史,讲达·芬奇画鸡蛋,要求同学们仔细观察,同学们画得很认真。可一周下来,没一个画得像样的,不是将鸡蛋画成了气球,就是画得像土豆。王画家急了,课堂上也就将话讲得没轻没重,什么笨呀、懒呀的也经常会从嘴里冒出来。恨铁不成钢的王画家以为他教得尽心,同学们会进步得快些,不料来上课的人却渐渐少了。
王画家只得又去找老管。老管挨家的去搜,上课的人又多了起来。王画家高兴了,说是要办个展览,把同学们近期的画展览一下,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同学们都说他们只画了些圈圈,没哪样好看的,都不愿拿出来。王画家一看不行,非得来点硬的,不然这画展真的就办不下去了,他硬性规定,每人必须拿出三张画,否则,就请镇上的领导硬性让他们再参加一次培训班。
收稿那天,王画家早早地就去了,他坐在椅子上等,同学们也来得很准时,进门都笑嘻嘻地看着他。王画家很高兴,微笑着看同学们往墙上挂作品,同学们也笑着看他。王画家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仔细一看,他坐过的地方,已留下了一个个黑屁股印。同学们哄笑起来,一溜烟地都往教室外跑去。原来,有同学做了恶作剧,将炭灰放到了王画家经常坐的椅子上。面对孩子们的恶作剧,王画家哭笑不得,还没等追出去,孩子们就耷拉着脑袋回来了,后面紧紧地跟着牧羊人似的老管。老管从后背上抽出长烟杆,使劲地敲着桌子说:“王老师是来帮助我们脱贫的,我学画的手艺都是王老师教的,他也是我的老师,你们不好好学,以后也不要到我这里来学画了。”老管说这话时,回过身来朝王画家拱了拱手,王画家也朝老管拱了拱手,引得孩子们哄堂大笑。这一招还挺灵,孩子们都乖乖回到了座位上,擦干净了炭灰,孩子们说他们的管老爹都画得那么好,管老爹的老师就更不得了,都争着将绘画作品小心地挂到展板上。王画家也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拿了出来。那一次展览办出了些影响,镇上几十里地的人都跑来观展,热闹了好一阵子,王画家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除了觉得自己干了件大事儿,也觉得老管这人很有意思,在这小镇上,吹拉弹唱打球照相,都能来那么一点,大人小孩都还挺买他的账。
就这样,王画家智力扶贫的想法渐渐走上了正轨。孩子们也都勤奋好学,几周下来,有的孩子竟然能够在墙体上、供桌上、木箱上画画了。以前,老乡们做好家具,要在上面做些图画,需要跑出几十里地到外面去请画师,现在画个箱子、供桌、柜子之类的,孩子们就可以完成了。王画家忙了几个月的智力扶贫项目,终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他的好心情也恢复如初,话渐渐多了起来。
老管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他眼中噙满的泪花,渐渐读懂了他对扶贫的理解。
老宅中的告别
这天,王画家一早就来找我,非要我陪他去看看老管,说是他特意托人从北京捎过来两条大前门香烟给老管。我们再次来到江西会馆,只见老管正在给一波前来参观的客人讲解江西会馆的历史。见了我们,微微地点了一下头,示意我们先坐在一旁休息。他讲得正起劲,他说娜姑原为彝语纳姑,意思是黑色的土地或广阔的原野。娜姑地处滇川古道要地,曾经是古代铸造钱币的地方,成就了历史上会泽的铜都地位。明清时期,娜姑古镇进入了鼎盛时期,涌入了很多外来的商人,促进了各地各省籍会馆宗祠的大量出现,渐渐形成了今天的格局。老管从明末清初建设江西会馆,讲到清乾隆年间朝廷依托这一带的精铜,大力发展冶炼技术铸造铜钱,开发政府的财政资源,维持大清王朝的运转。他从青楼女子的眼泪,讲到天主教堂的钟声;又从青楼与教堂并存的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讲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精彩至极,让我们几乎忘了来这儿的目的,完全听入了迷。
好不容易送走了客人,已经快天黑了。王画家坚持要到老管家里去看看。一路上,老管走得飞快,我和王画家要小跑才能跟上。老管像换了个人一般,完全没有了刚才讲解娜姑历史的风趣,没讲一句话,只顾低着头走路。好像除了娜姑的江西会馆、教堂、奇闻轶事外,老管嘴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话题。
老管住的是间木制房子,四面用木板严严实实围了起来,为了保暖,没有开大的窗户。一束阳光正好从屋顶的一片亮瓦上射了进来,就像舞台上的追光。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慢慢适应过来,终于看清楚了老管家的摆设。一个石块砌成的火塘已被烟熏得乌黑,火塘上烧着一把茶壶,正在冒着热气,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火塘边忙碌。见我们进来,连忙起身,咧开嘴冲着我们笑了笑。老管向我们介绍,这是他的妻子。由于身体不好,只能照管一下家务,也不太料理田地间的农活了。
老管见我们站着,用袖子在木墩上擦了擦,尴尬地冲我们笑了笑,示意我们坐下。我们在木墩上坐了下来。王画家拿出香烟,郑重地递到了老管的手上,说这是一点心意,他近期就要回北京去了。这段时间以来,他没少麻烦老管,他邀请老管在合适的时候,带着老伴到北京他的家里去做客。王画家说得很真诚,听得人心里酸酸的。
老管执意不收王画家的香烟,我在一旁劝了好久,他才松了口,转身进了里屋,窸窸窣窣翻了半天,拿出了一个珍藏多年的斑铜老花瓶来,一定要送给王画家做个纪念,不然他就不收王画家的香烟。王画家只好收下。
我慢慢端起老管送上的茶水,茶已有些凉,喝在嘴里涩涩的。直到此时,我才仔细端详了老管的住宅。这是一处很典型的滇东民居。木质的框架,屋顶上供家猫出入预留的猫耳洞,玻璃做的采光瓦,大红供桌上精致的木雕,处处都透露出古朴精致的滇东建筑风格。我仔细打听才知道,老管的上一辈在当地已经算得上是有名的文化人,很受人们的尊敬。他这宅子,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够得上分量的老宅子了。
我对老管说:“上面有政策,只要有价值,可以对一些古旧建筑物进行保护性修复,你这老宅子很有特点,是滇东一带的代表性民居。可以向上面有关部门申请一点经费,把老宅子好好修一修。”老管下意识地瞟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这老宅子已经传了几辈人了,现在这么破旧,确实该修一修了。可是这镇上的老宅子多得很,大家都争着要修理,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经费?”何况他搞的工作和这个保护修复的总有些关联,如果放着别人家的老宅子不管,自己先争取了国家的补贴,就是将老宅子修复得再好,别人也会有闲话的,还是先放一放吧。
望着老管那光线昏暗的老宅子。我和王画家苦口婆心轮番跟老管讲了很多道理。我讲这老宅子的历史地位,王画家讲老宅子的艺术价值,修缮的必要性、可行性。我们说那么多话的目的,无非是想借着有关政策,把老管的老宅子好好修缮一番,也算是对老管的一种报答。
老管静静地听着,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仿佛没听到我们说了什么,半天也没说话。我和王画家一个劲地讲,老管一个劲儿地在抽烟。我和王画家对望了一下,也不便再说什么。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我们三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我们既为这老宅子的命运担忧,又为老管的那种境界感到自豪。屋子里只有老管抽烟吧嗒吧嗒的声音。静静地坐了一会,我们起身告辞,老管将我们送出了很远。那晩的月色很好,我们心里却是非常沉重。
十多天后,老管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们,说他的老宅子已经开始修缮了,让我们去看看,帮他参谋参谋,出出主意。我和王画家都很诧异,连忙赶了过去,老宅子的修缮正干得热火朝天,房前屋后摆满了木料和砂石砖瓦。我们问了邻居后才知道,原来老管把祖上留下的四根柏木变卖了,换了木料和砂石,请了工匠对老宅子进行修缮。我们知道那四根柏木是老管的至爱之物,相伴了老管几十年。没事的时候,老管总是喜欢轻轻地抚摸它们,天长日久,柏木都被磨得光滑锃亮。老管说他是抚摸祖上的恩德,悼念那些逝去的亲人。在老管眼中,柏木就是他的灵魂,他的命根子。
老管依然吧嗒吧嗒抽着他的烟。我一把抓住老管的手问:“你怎么可以把这柏木卖掉呢?有什么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这样怎么行?你赶快去跟人家好好说说,或者赔偿人家点损失,一定把柏木要回来。”老管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他眼中噙满的泪花,渐渐读懂了他对扶贫的理解。
扶贫的日子结束了。当年在王画家扶贫培训班上参加培训的孩子,大多已经长大成才,有的当了教师,有的成了农业专家,还有的被选为了村干部,正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大展宏图,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而我们几个的那些往事也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作者:杨卓成
任职于云南省曲靖市文联,曾出版长篇小说《白粉》《生命有约》《血线》《山河无语》等
